
作者: (好意思)罗纳德·博格爸爸的乖女儿,打飞机,口交还让禸#萝莉
出书社: 南京大学出书社
出品方: 南京大学出书社·祈望者
译者: 石绘
出书年: 2022-1

一、内容简介
《德勒兹论体裁》是一册研究德勒兹体裁论著的空洞性导念书。通过对德勒兹商议体裁的中枢文本的清雅辨读,博格在各章节分别西席了萨克-马索克和卡罗尔作品中的疾病与健康,普鲁斯特作品中的符征,卡夫卡的体裁机器、“次要体裁”的主见,卡尔梅洛•贝内的次要戏剧,以及T. E. 劳伦斯和贝克特的“视觉与听觉”,由此对德勒兹研究写稿艺术的措施提供了一套了了而系统的阐释。

《德勒兹论体裁》把这些研究与其他散见的诸多文本纳入一语气德勒兹一皆想想生存的一般性研究经营中:将体裁看作一种健康,将作者视为文化的大夫。
二、作者与译者简介
作者简介:罗纳德•博格(Ronald Bogue,1948— ),好意思国佐治亚大学相比体裁系荣誉退休老师,德勒兹群众。代表作有《德勒兹与瓜塔里》和“德勒兹与艺术”系列(《德勒兹论音乐、绘制与艺术》《德勒兹论体裁》《德勒兹论电影》)等。
译者简介:石绘,中国东谈主民大学体裁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好意思学研究,译有《新生》(合译)。
三、文籍目次
缩写表 / 1
导论 / 1
第一章 疾病、符征、趣味 / 10
讲明和评价 / 11
马索克和受虐恋 / 17
趣味和名义 / 27
第二章 普鲁斯特的符征机器 / 40
符征的辐散和讲明 / 41
符征的再讲明 / 50
符征的生息与分娩 / 56
机器 / 64
第三章 卡夫卡的法律机器 / 73
理想机器和理想分娩 / 74
何谓机器?/ 78
光棍机器 / 85
写稿机器 / 92
法律机器 / 98
艺术和人命 / 107
第四章 次要体裁 / 111
小众体裁 / 112
解域化的说话 / 115
说话和力量 / 119爸爸的乖女儿,打飞机,口交还让禸#萝莉
说话的次要使用 / 122
声息和趣味 / 126
请教的集体安设 / 132
第五章 克莱斯特、贝内、次要戏剧 / 140
克莱斯特和干戈机器 / 141
干戈和彭忒西勒亚 / 147
贝内的理查 / 154
淫秽的历史 / 160
德勒兹的贝内 / 167
戏剧和东谈主民 / 178
第六章 人命、澄莹、视觉、听觉 / 183
逃遁线 / 184
线 / 188
视觉和听觉 / 196
视觉、轨迹与生成 / 206
终曲:贝克特的电视剧 / 213
论断 / 226
参考文件 / 233
译名对照表 / 237
四、精彩书摘
理想机器和理想分娩
在《普鲁斯特与符征》1970版的增补部分中,德勒兹指出,和其他当代艺术作品一样,《回想》的功能大于其趣味:“当代艺术作品没故趣味的问题,唯有使用的问题。”(PS 176; 129)分析者应致力于对作品的组成部分偏激启动进行描画,而非揭示作品的守密趣味。

在这个趣味上,艺术作品是一部机器,似乎并莫得深度或灵魂,只是一部要么使命要么不使命的用具良友。机器主见并非德勒兹在《普鲁斯特与符征》中的中枢温煦,唯有到了《反俄狄浦斯》,这一主见才得回拓展性的阐发。在这部著述中,不惟艺术作品,世间万有皆被视为机器。“机器无处不在,这绝非从隐喻趣味来说:它们是机器的机器,相互配接,相互伙同。一部器官机器接通一部源头机器(source-machine):其中一部机器发出一条流,另一部机器则割断它。”(AO 7; 1)这些机器是“理想机器”,是“理想分娩”一般进度中的组件,而理想分娩这一主见被德勒兹和瓜塔里用来指代一种鼓胀着感兴的无所不在的行动。[1]
[1] 德勒兹和瓜塔里借助“理想机器”这一主见将弗洛伊德的理想和马克想的分娩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亦然对二者的修改。他们对分娩的强调包含了广博的行动流程和能量畅通中商品的分娩、交换、分派和赔本等传统主见。他们之是以觉得理想无处不在是因为他们莫得将理想描画为匮乏,而是描画为感兴或强度,一种诸元素的相互感兴,借此,力比多化的物资、能量和信息之流在相互之间穿行。对于理想分娩的富余启发的敷陈,极端参阅Massumi,Goodchild,Deleuze and Guattar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s of Desire,以及Holland,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o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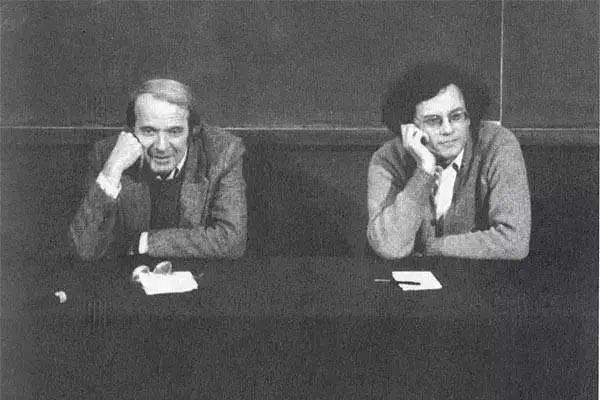
德勒兹和加塔利
弗洛伊德将灵魂分裂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对此,德勒兹和瓜塔里以带着几分戏谑的方式进行了恢复,他们辨识出理想分娩的三个基本组件,即理想机器、无器官的体魄和游牧主体,每个组件与理想分娩的特定阶段相联结——分娩的分娩(理想机器)、刻写(inscription)的分娩(无器官的体魄)和赔本/完成(consumption/consummation)的分娩(游牧主体)。婴儿吮吸母乳就是理想机器的一个爽脆模子。嘴巴机器与乳房机器相等接,母乳之流穿越乳房机器到达嘴巴机器。婴儿的嘴巴机器转而与消化谈的各式机器相等接(食谈机器、胃部机器、肠谈机器、尿谈机器、肛门机器),营养之流迟缓革新为婴儿体内诸旁系理想机器的各式能量回路(血液轮回的、神经的、荷尔蒙的等等),最终呈现为排泄物之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
从乳房机器自身而出的奶水之流来自营养回路,这个营养回路上溯至母亲嘴巴机器摄入的诸多营养物。因此,理想机器在诸流横穿而过的链条和回路中相互配接,每一个回路蔓延至其他回路,后者又扩散成延续拓展的行动网(如母亲营营养娩行动中所固有的诸多回路,婴儿排泄物领会行动包含的微生物回路)。
但是,婴儿的嘴巴机器并不单是是饮食机器。它已经呼吸机器、吐痰机器、呼喊机器等等。在这个趣味上,每个理想机器都有“一种设置[machiné]并储备于其中的编码”(AO 46; 38),它是对特定回路进行章程的革新机制,这种机制于特定期间在特定回路中证据作用。进而言之,任何理想机器的回路都无法与其他回路分离而单独存在,例如,婴儿的营养回路与视觉回路连结(如婴儿的眼睛机器提神着卧室的台灯),与感觉回路连结(鼻子机器与厨房气息之发配接),与触觉回路连结(皮肤机器战争热量、纤维、肌肤、薄雾、气流)。要是咱们把统统这些回路进行描摹,就像弥远的线条在单个名义上,网状的名义将会组成一具无器官的体魄,这是对于共存的诸回路(在所例如子中,这些回路就是营养、视觉、感觉和触觉回路)和交互且分离的诸回路(消化、呼吸、叫喊回路)的单幅舆图。需要指出的是,无器官的体魄不成与某个归并的通灵体魄图像(a unified psychic body image)相混浊。最初,它的回路无尽地拓展,超过任何申饬性体魄轮廓。

例如,假使咱们平常地探究“婴儿的”无器官的体魄,咱们必须将母亲的乳房、卧室的台灯、厨房的气息、使食品转机为营养物和排泄物的微生物等等纳入这具无器官的体魄之内。其次,它不组成任何平庸趣味上的归并体。它包含着结合和分离,后者亦即在某些情况下共存配合而在其他情况下相互接替、取代或扞拒的异质性回路。理想分娩“是患难之交的复多性,即不成简化为归并性的坚信”,要是咱们在无器官的体魄中遭遇一个“举座”,这亦然一个“与部分并行的总体性,这是属于诸部分却不整合它们的举座,是属于诸部分但不统合它们而况当作分开组成的新部分添加给它们的归并体”(AO 50; 42)。[1]
[1] 《反俄狄浦斯》明显地阐发了无器官的体魄的归并性与普鲁斯特《回想》的归并性之间的干系:“因此普鲁斯特说举座是被分娩出来的,它我方是当作诸部分傍边的一个部分而被分娩出来的,它既不统合也不整合,它自身之是以妥当诸部分只是在于它在非雷同的瓶子之间建筑越轨的通谈,在诸身分之间建筑横穿的归并性,这些身分在它们各自维度上保留着它们一皆的各别。”(AO 51;43)
第三,它不是患难之交的幻想或心灵图像。毋宁说,它是潜在实体,即未成为试验的确凿物。在某种趣味上,它被理想机器当作后发服从分娩出来,但在另一种趣味上,它是先于理想机器启动的可能性情状,即任何给定的理想机器之链在某个特定本事可能将之杀青出来的潜在回路之网。

《德勒兹论体裁》书影
从理想机器和无器官的体魄的相互作用中出生出两种复合机器,咱们称之为“偏执狂机器”(paranoiac machine)和“神迹化机器”(miraculating machine)。无器官的体魄并非莫得器官,而是莫得司法的和固定的有机组织。它是一种反有机组织、一种分离式空洞,是一部捏续损坏、卡壳、冻结和崩解,从而拆分和打断理想机器回路的反分娩的机器,但同期亦然一部将各式理想机器相互议论在复多的以横贯方式伙同着的诸回路中的机器。当理想机器将无器官的体魄当作某种迫近的总体性,当作某种恣虐性秩序而加以摒除时,就产生了偏执狂机器。当理想机器眩惑无器官的体魄,仿佛它们是其神奇名义的懒散物时,就出现了神迹化机器。[1]由于无器官的体魄既分娩分离又分娩空洞,既分娩领会又分娩组合,因此偏执狂机器和神迹化机器当作理想分娩的无尽扭捏情状而共存,捏续延续地相互反应。
[1] 德勒兹和瓜塔里从丹尼尔·保罗·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著述中取用了“神迹化”一词,后者在其《我的神经疾病回忆录》(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一书中描画了其体魄被天主之光“神迹化”的各式方式,例如,他“在莫得胃、肠,险些莫得肺,食谈扯破,莫得膀胱,肋骨幻灭的情况下存活了很久”(引自AO 14; 8)。

第三种理想机器是游牧主体,“一种奇异的主体,莫得固定身份,飘摇在无器官的体魄中,老是伴跟着理想机器,由其从被生居品中取出的份额所章程,无处不在地鸠合着某个生成或某个化身(avatar)的报偿(reward),从它赔本的情状中出生并伴跟着每个新情状新生”(AO 23; 16)。要是将无器官的体魄视为一个被理想机器的回路分裂为网的名义,游牧主体则是沿着刻写于名义上的各式旅途而在各处暴露的出格点(errant point),它是附庸的赔本机器(法语的consommation既指经济上的赔本,又指力比多的完成)。[1]
[1] “无器官的体魄是一个卵:它被轴线和阈值、维度、经度、测地线所横穿,被象征住生成和通谈的梯度所横穿,这些梯度是它在那边发展的止境……唯有强度带、潜能带、阈值带和梯度带。”(AO 26;19)。这一通谈的说话取自胚胎学中对胚胎沿着由其名义的能量各别所章程的测地线自我分裂的描画。德勒兹常常引述达尔克(Dalcq)的《卵偏激组织活力》(LOeuf et son dynamisme organisateur)当作这些主见的出处。
游牧主体通过第三种复合机器——“光棍机器”——的造成而被创造出来。光棍机器是“理想机器和无器官的体魄之间的一种新纠合,它产生出一种全新的东谈主类或光泽的有机体”(AO 24; 17)。光棍机器所产生的是“患难之交情状中的密集的量(intensive quantities),这种量级达到险些令东谈主无法承受的程度——遭受到最高点的光棍的可怜和光泽,就像一次悬搁在生与死之间的叫喊,一种病笃过渡(intensive passage)的感受,被洗劫了其形态和模式的患难之交情状和原始内张度”(AO 25; 18)。

菲利克斯·加塔利(1930-1992年)
无器官的体魄组成了某种零度(zerodegree)强度,理想机器在其启动流程中象征感兴强度的各个层级。在偏执狂机器中,理想机器和无器官的体魄相互摒除,在神迹化机器中,它们相互眩惑,但在上述两种情形中,理想机器都细则了正的强度层级。在摒除和眩惑的扭捏中,产生了诸强度层级中的各别,产生了从一个病笃情状到另一个病笃情状的过渡,而在每个过渡中都出现一个游牧主体,理想机器和无器官的体魄随之插足一种新的干系之中,一种新的功能启动也随之而生,它通过光棍机器的造成而对偏执狂机器和神迹化机器之间的摒除和眩惑进行“融合”(reconciles)。[1]
[1] 在《弗兰西斯·培根》中,德勒兹同样将“临时器官”界定为一个强度层级向另一个强度层级的通谈(FB 35)。游牧主体和临时器官的等价应该反对任何将游牧主体等同于传统的灵魂或意志的作念法。
好看的日本av“质言之,眩惑力和摒除力的对立产生了诸强度身分的某种怒放系列,它们都是积极的,毫不抒发某个系统的终极均衡,而是抒发某个主体横穿而过的大都固定的亚稳态。”(AO 26; 19)
艺术和人命
卡夫卡的写稿机器包括三个组件,即书信、短篇故事和演义。卡夫卡的问题在于保捏机器的启动,在于通过造成理想分娩的怒放回路去创造和保管畅通。尽管在保捏书信流朝向未婚妻的流动和写稿对于永动流(perpetuation of flow)的故事与演义之间似乎存在着根柢各别。但德勒兹和瓜塔里觉得在卡夫卡那边人命和艺术之间并无对立。他们发现,“在卡夫卡那边将人命和写稿进行对立的作念法,以及测度他由于在面临生活时匮乏、恇怯、窝囊而在体裁中寻求避风港的读解法是如斯令东谈主气恼,如斯情有可原。没错,一个块茎、一个地洞,但绝非一座象牙塔;没错,一条逃遁线,但绝非一个避风港”(K 74; 41)。

弗兰兹·卡夫卡(1883-1924年)
德勒兹和瓜塔里指出,书信、短篇故事和演义通过多元的一语气式伙同行动而相互雷同,终结,审判机制出咫尺统统三个组件之中,费利斯生成-狗的畅通将书信和短篇故事伙同起来,来自演义的科层安设则浸透短篇故事的机器索引中。东谈主们可能争辩谈,这只是标明人命和艺术在作者意志中是相互影响的,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转头陈词是,不管卡夫卡是在写“确凿的”信件已经在写演义,写稿本人都是扩展的社会机器之内的一种“机器启动”行动,写稿只是此社会机器的一部分。卡夫卡探询社会边界,将各式机器安设组件之间相互伙同的干系绘成图表,而况“知谈将他与抒发的体裁机器连结的统统模式,他既是这部机器的齿轮、技工、操作员,亦然它的受刑者”(K 106; 58)。正如在《审判》中每个东谈主都与法律相伙同,卡夫卡我方也同样位于干系网之内——法院的、科层的、政事的、买卖的、艺术的、家庭的等等——统统这些都当作机器安设而启动,而况不管他是在给费利斯写信抑或写稿对于K的演义,他的写稿机器都与这些社会机器啮合。

当卡夫卡写稿时,他是在行径,因为写稿是广义的社会行径场域之内的一种行径,在这一场域中,话语和非话语交汇在实行、畅通和变更的相互感兴模式中。因此,卡夫卡的写稿并非只是是对外部寰宇进行心灵表征,也不是对经济基础试验进行表层建筑的好意思学挑剔:“任何东谈主都不要说[解域化之]线只是在精神中[en esprit]露出。仿佛写稿也不是一部机器,仿佛它不是一种行径,以至沉寂于它的出书物,仿佛写稿机器也不是一部机器(与任何他物一样不属于表层建筑,与任何他物一样不属于意志形态),如今在本钱宗旨机器、科层体制机器或法西斯机器中被占用,如今标画某种限度的创新道路。”(K 109; 60)当卡夫卡写稿时,他并莫得从寰宇中撤退,而是在其中行径:“房间非但不是他当作作者的隐遁之所,反而为他提供了双重之流:其一是领有宏伟过去的科层体制之流,它与处于自我造成流程中的确凿安设接通;其二是处于以最通行和试验的方式[en train de fuir à la façon la plus actuelle]进行逃离之流程中的游牧之流,它与社会宗旨、无政府宗旨、社会畅通接通。”(K 75; 41)
在《普鲁斯特与符征》中,德勒兹将《回想》视为一部其趣味远逊于其启动的机器。

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年)
在《卡夫卡》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卡夫卡的写稿视为一部由三组件组成的与弥远机器啮合的机器。正如他们在《反俄狄浦斯》中所详论,机器的骨子是造成伙同式、分离式和联结式空洞,割断/伙同诸流,在包纳性分离中近似诸流,以强度之游牧式波动的方式对诸流进行陈设。机器“启动着”,它们创造了回路而况是回路的一部分。这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卡夫卡那边发现的机器的骨子。

《反俄狄浦斯》英文版封面
他们说,他的才华“在于将男东谈主和女东谈主视为机器的部分,这不仅体咫尺他们的使命中,在左近行动中更是如斯,在休息中,在恋爱中,在抗辩中,在气愤中,等等”(K 145; 81)。对于卡夫卡而言,“理想永不啻息地在机器中制造一部机器[原文为“在机器中制造机器”,faire machine dans la machine],且沿着已有齿轮去建造新的齿轮,用之阻挡,即便这些齿轮似乎相互拒抗或以某种不和谐的方式启动。严格来说,恰是伙同行动,统统对拆卸进行带领的伙同行动制造了机器”(K 146; 82)。
在《普鲁斯特与符征》中,德勒兹指出《回想》是一种复多性,是一部机器,其举座是当作与其他部分并行的添加部分而被分娩出来的,普鲁斯特将其作品比作一个大教堂,比作一件连衣裙,但德勒兹指出大教堂从未竣工,连衣裙则是永恒处于缝缀流程中的拼合物。

此复多性的“一”(oneness)的造成是通过使歧异系列和顽固瓶子相互雷同的横断面而造成的。相较而言,卡夫卡的机器更了了地自大出某种复多性,他的作品组成了一个地洞,就像《地洞》中鼠类生物的栖息地,纯碎迷宫似的相互伙同,莫得明确的入口和出口,领有弥远逃离道路。地洞是一个块茎,就像杂草一样,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点的增生,其中任何极少都可与其他点相互伙同。卡夫卡的书信、短篇故事和演义是这一地洞的纯碎,是杂草块茎的诸茎节,日志则“是块茎自身”,即“卡夫卡暗示不想离开的身分(从环境的趣味上来说),就像鱼离不滚水”(K 76; 96)。书信、短篇故事和演义相互伙同,每个组件都通过造成伙同、开启和保捏畅通来启动。写稿机器既是一部纯碎挖掘机又是所挖掘的纯碎本人,既是一部“块茎蔓生”(rhizoming)机器又是蔓生造成的块茎本人。而况,机器愈完好,就愈处于未完成情状中。当婚配圈套闭合时,书信之流就停滞不动;在短篇故事中,逃遁线被堵塞(《变形记》),唯有通过一部不解确的机器的索引才调得回邋遢的指引(《对一条狗的探询》),大约被孤苦在一部与社会场域相分离的机器的抽象启动中(《在放逐地》);但是在演义中,机器充分启动,伙同方式各种化且无尽膨胀。自成一体、构想完整的短篇故事,如《变形记》,是地洞中弥远的末路。

卡夫卡著述《变形记》插画
而未完成的演义则是允洽启动的掘洞机器,永无停止地挖掘地洞。机器的功能是启动,它在启动神色必创造某种怒放的复多性。齐全成型的完整机器是一个未完成的引擎。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到卡夫卡的写稿机器时所说,“从未有东谈主创造过如斯完好的由畅通所组成的一件作品,这些畅通被一皆中断但又一皆相互雷同”(K 74; 41)。
卡夫卡的写稿机器不是用来讲明的,而是用来描画的。它的趣味远逊于其启动,而况其启动使我方成为一种怒放的复多性,一个膨胀的地洞或蔓生的块茎。写稿机器被镶嵌社会机器并被后者横穿而过,它的启动与广博的理想分娩流程相互伙同。从这个方面来说,它径直具有政事性,其启动发生在某种集体行动场域中。说话以何种方式在这么一部机器中证据作用,这是仍待胪陈的问题。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卡夫卡视为“次要体裁”的践行者,这种体裁具有径直的政事性,其说话受高度解域的感发并通过请教的集体安设而被抒发出来。正如咱们将不才一章中所见,次要体裁触及说话的某种次要使用,而况这种诈欺在次要写稿机器的启动中至关遑急。
(文中图片开端于麇集)爸爸的乖女儿,打飞机,口交还让禸#萝莉
